

我出生在古徽州婺源县清华镇(今属江西)。清华以“清溪萦绕,华照增辉”得名,唐开元二十八年(740)婺源建县,县治就设在清华,历时161年。幽深的清华古街穿过镇子中央,狭隘而悠长。两边形制古朴的店铺鳞次栉比,二层藏有木雕的飞檐,把阳光裁剪得半明半暗。古镇的青石板街面曲折蜿蜒,每每走到尽头,却发现转弯处又是长长的古街,幽深复幽深。
我家老屋立古街,出院门往左约百米便可看到一河滔滔,河上建有廊桥,名叫彩虹桥,造于南宋。桥竣工那天傍晚,西山上出现一道彩虹,夕阳透过云层,彩虹倒映河中,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,故得名。桥上刻一楹联:“两水夹明镜,双桥落彩虹。”远处青山如黛,桥下鱼翔水底,站在桥上,极目眺望,田园风景触目皆春。
我的童年在清华度过,清华是我的故乡。故乡的土地、河流、山脉,甚至那悠悠转动的水车、雨天里布谷潮湿的鸣叫,连同我在廊桥上、河滩边踩出的野性脚印,全都落在我的身心里了。
迄今我创作的两千多首童诗,水井、桥、河流、白鹅、大公鸡、小羊、燕子、蜗牛、画眉鸟、天牛等等,乡村的景和物遍布诗行。创作时,兴之所至,并未刻意,回眸抚摸,多是散发着田园气息的童年旧事、旧物、旧景,应是涌自深如海的潜意识吧。
就以彩虹桥为例。那桥、那彩虹,浸入我的童心、溅入我的生命里。我的童诗,彩虹与桥的形象,多有呈示,其源盖出于此。如《彩虹云·彩虹鱼》以彩虹为支点,撑起全诗的诗情画意:“天上的云在河中,河里的鱼在天上;云变成了水中的彩虹云,鱼变成了天上的彩虹鱼。彩虹化为云、化为鱼,从我的童年记忆里游来。”
同样的创作机杼织出《七弦琴》:“太阳有七种颜色,/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紫、蓝。/彩虹是太阳的七弦琴,/挂在天边——/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紫、蓝。/一种颜色是一根琴弦。”彩虹与“七弦琴”珠联璧合,上演了一出刷新读者审美视野的情景剧。活在我童年里的“彩虹”,童心浸染,诗心过滤,七色彩虹蜕变成七弦琴。诗的意象是熟悉的陌生,恰如雪莱所言:“诗剥去笼罩在世界隐蔽的美容上的面纱,让熟悉的事物变成仿佛不熟悉的。”
《故乡的河》以“彩虹桥”为诗的主干意象,展开叙事和抒怀:“早晨,/我从彩虹桥这头跑到那头,/看太阳升起。/傍晚,/我从彩虹桥那头跑到这头,/看太阳下山。/踩在彩虹桥上的/童年脚印,/被一场大雨冲进河里去了。/雨后,/河里多了好多好多条鱼,/扑腾、扑腾、扑腾……”
远隔千山万水的童年时空,连同那廊桥,被我的回忆之网,捕捞进湿漉漉的诗行。
不只故乡的景物挪入诗,故乡的以童年为背景的世俗生活也植入了我的诗行,凸显童年情绪记忆。我的入选《中国儿童文学百年百篇·童诗卷》中的《细雨打湿的记忆》,写的就是童年在故乡上学的情景。清华镇的古街分为上街、中街和下街,我的家在上街,清华镇小学建在下街,一棵巨大的古槠树巍然屹立于校园。1954年,我在清华镇小学读书,下雨天打着油纸伞上学,不远处有牧童头戴斗笠雨中放牛,这一场景镌刻在心,童年的记忆从诗心汩汩涌现——
“雨天长满白花花的胡须,/回忆是一把剃刀。
记得风雨中的绿色阡陌,/戴一顶斗笠骑在牛背上横笛劲吹,/童年的雨声沿笠檐滴下,/流进笛孔,/我袅袅吹出——/湿漉漉笛声被布谷鸟衔走了。
犹忆靠着村小的篱笆墙,/打一把油纸伞撑起一片丽日晴空,/少年的雨声顺伞沿滴下,/滚落翻动的书上,/我朗朗读出——/潮乎乎的书声被放学的钟声汲去了。
雨天长满绿盈盈的草儿,/回忆是一把镰刀。”
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艾略特言道:“一个诗人的想象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他的阅读。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就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。”那位宣告“儿童是成人之父”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,更是直接指明,“不朽的暗示来自童年时期”。我深以为然。童诗从童心来,童心从童年来,童年从故乡来。故乡丰饶的水啊,浇绿了我的童诗。
撰稿:戴达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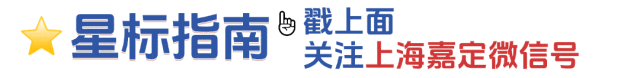


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