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剑乐言《小王子》,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知道的事情,但我没想到他居然因此写出了一本书。当年,我是受梁剑的影响才知道并去阅读《小王子》的,不过青年时代陷入生计,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女儿小学三年级时,我为了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家校协作任务,到她的课堂上分享一本书,于是又想起梁剑常说的这部老少咸宜的《小王子》,重新阅读并与一群懵懂的儿童叽叽喳喳地讨论了一番。当时说了什么,我早已忘却,但经此一遭,《小王子》于我又多了一份“最难风雨故人来”之感。这次,“小王子”又翩然而至,二十年来仿佛轮回,我再次面对“小王子”,有所不同的是,这次是《哲学家的小王子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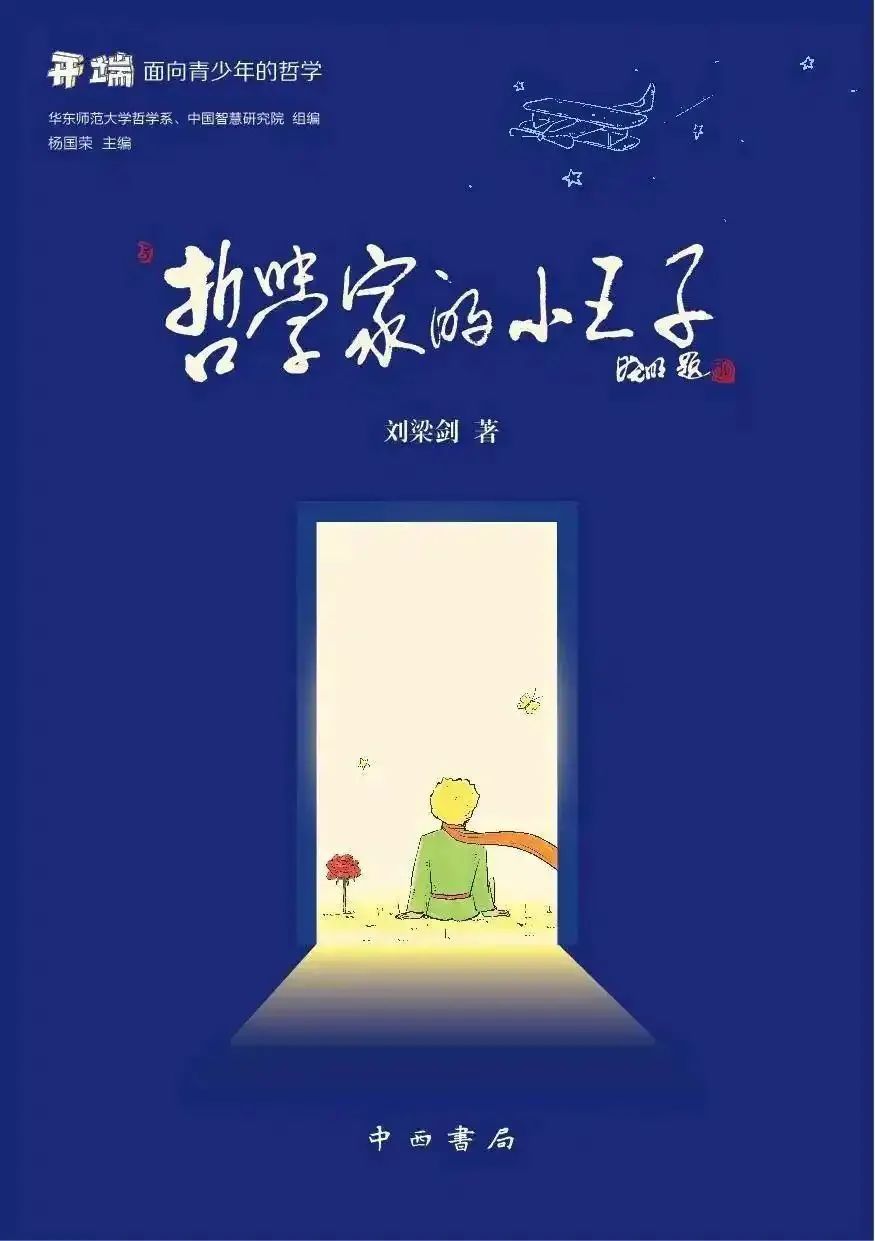
《哲学家的小王子》
刘梁剑 著
中西书局 | 2025年5月
诗人写诗,一切事物皆可入诗,天地风霜、草木山川、鸢飞鱼跃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世事人情、往古来今,几乎没有什么不入诗人之眼。可是眼下学院里的哲学工作者写文章,似乎有其特定的对象,除了以哲学术语进行理论书写之外,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对既定的哲学文本进行诠释和分析,这也是我们目前哲学训练和哲学书写的主要路径,哲学工作者们都自觉地恪守学术规程,用专业的术语、概念、命题反复揣摩着流传下来的思想文本。作为一个从业近三十年的学院派哲学工作者,梁剑当然非常熟悉哲学规程的界限所在,好在他没有以此“自限”。“自限”是梁剑自己的话。大约十年前,他曾经提出“以儒家自居还是以儒家自限”的问题。虽然他这个话是针对“儒学复兴”的文化现象而说的,但我一直觉得“自居还是自限”的提问方式可以用在很多场域。比如,对于哲学工作者的学术工作来说,是以阐释哲学史上的文本自居还是自限? 显然,能够精深地阐释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文本是哲学工作者的立业之本,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下,若没有这个能力,大概是难以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找到一份研究哲学的工作的。然而哲学工作者是否要以解读“纯化”的哲学史文本自限? 答案显然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。“无必要”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的开放性,哲学思想蕴含在一切可以解读的文本、事物之中,我们没有必要仅仅把目光局限在传统的哲学史意义上的文本中;“无可能”是因为随着人们阅读和理解对象的扩大化,既存的哲学文本已经不能够满足哲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关切,必然要不断地扩展研究对象。由此而言,哲学工作者所深耕的“文本”不断“泛化”是势之所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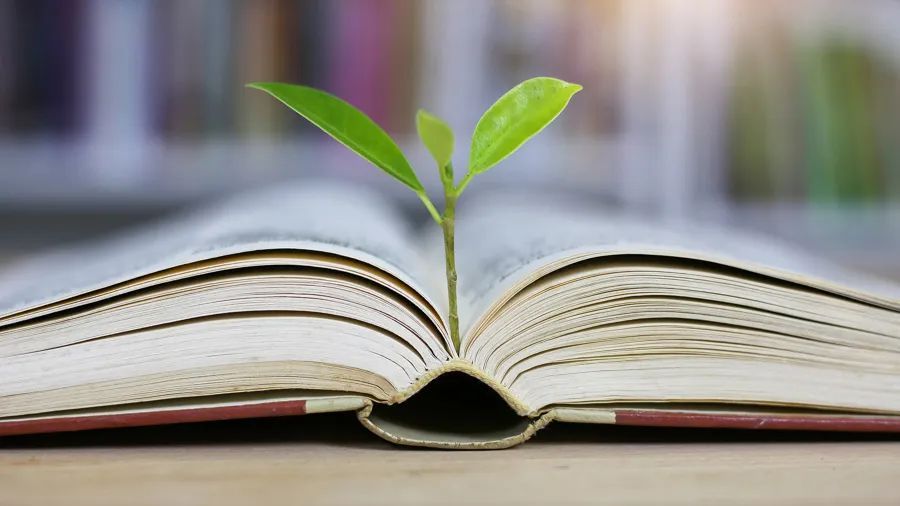
梁剑没有以解读哲学史文本的哲学工作者自限,而更像是一位不断开疆拓土的思想骑士,他这次开拓的新疆域是《小王子》。《小王子》显然不是“纯化”的哲学文本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《小王子》是一部童书,故事在小王子“排空驭气奔如电,升天入地求之遍”的飞行中展开,是儿童眼中奇幻的“星际旅行记”。但这部“星际旅行记”,同时也是一部哲学意义上的“童心”之作,描绘了“应然世界”对“实然世界”的童幻抵抗:世界本该如此,虽然还不如此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梁剑将《小王子》引申为“哲学家的小王子”,对书中的“驯养”“责任”“友谊”等话题乃至伦理精神作了哲学阐发,进而将阐发《小王子》变成了哲学工作者的“正事”。梁剑没有以解读“纯化”的哲学史文本“自限”,我们才有了这部有趣的《哲学家的小王子》。
“对你驯养过的东西,你永远负有责任。”梁剑“驯养”《小王子》已经二十多年了,他也有“责任”对这部书作一次哲学的阐发。虽然梁剑在书中每一章的标题下都引用了老庄话语,出尘脱俗,然而人间世上毕竟有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”的责任。最近几年梁剑太忙,似乎对于熟和不熟的事务都负有责任,如果他能够稍微闲一点的话,《哲学家的小王子》会写得更加“神采奕奕”。
作 者:
朱 承
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
来源:中华读书报